复旦大学美国史读书会:《这个暴力的帝国:一种美国国家身份的诞生》
复旦大学美国史读书会
2019年第1场
本文为复旦大学美国史读书会2019年第1场内容,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鲁迪秋整理与编辑。经发言者审定,本文已授权“美国史研究”公众号全权刊发。文中所用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如需转载,请注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官方公众号“美国史研究”】,感谢关注本号!
时间:2019年4月24日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1907室
主持人:鲁迪秋
书目与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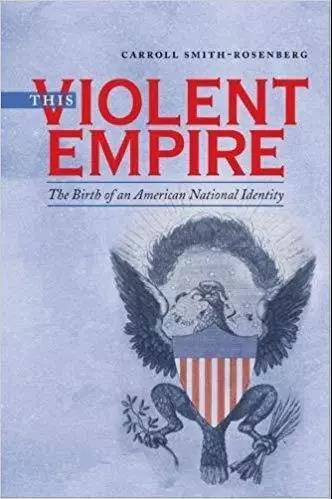
本书介绍:美国人是谁?谁又是美国人?诞生于一场革命的美利坚共和国该如何树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身份,从而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们联合起来?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在《这个暴力的帝国:一种美国国家身份的诞生》一书中为我们做出了解答。
史密斯-罗森堡爬梳18世纪末的政治杂志与小说,向我们展现了当时政治精英所构想的三种美国人形象:共和国公民、美利坚人与资产阶级绅士。为了加强国家身份内部的稳定,明确身份的边界,他们构建了相应的他者群体:马萨诸塞西部反叛的农场主、女性、印第安人、黑人奴隶。在政治精英看来,只有经济独立、拥有美德的中上层白人男性才是美国人。但是,这些被“他者化”的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并不愿顺从地接受政治精英的安排。西部农场主与女性也要求获取公民身份,印第安人则实实在地存在于美洲大陆而不容无视,奴隶制更是腐化了所有参与奴隶经济的人。因此,这三种美国国家身份并不像政治精英所希望的那样界限分明,其不稳定性导致了修辞暴力的产生。
在现实关怀的引导下,史密斯-罗森堡借用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追溯美国国家身份不稳定性的来源,揭示美国人国家身份构建方式及内涵的暴力性质。
作者介绍: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是美国妇女史和性别史的先驱,研究成果丰硕,享有很高的学术威望。她于1968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是她的论文指导教师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起至1996年,她同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精神病学系和历史系任职,参与创建了该校的“性别、性与女性研究项目”(Gender, Sexuality, and Women’s Studies Program)。从1996年开始,她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担任玛丽·弗朗西丝·贝里历史、女性研究与美国文化大学讲席教授(Mary Frances Berry Colleg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Women’s Studies and American Culture),直至2008年退休。她早年在《符号》(Signs)上发表的文章《充满爱和仪式的女性世界:19世纪美国女性的关系》("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 Relations between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奠定了女同性恋历史研究的基础。尽管她关注的是妇女和性别,她的着眼点仍在政治、政治文化与政治观念。除本书外,史密斯-罗森堡还著有《宗教与美国城市的兴起:1812至1870年期间纽约市的传教运动》(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City: The New York City Mission Movement, 1812-1870, 1971)、《目无法纪:维多利亚时期美国的性别构想》(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1985)。
话题交流
开场白
鲁迪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的《这个暴力的帝国:一种美国国家身份的诞生》。我想先从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使用的材料等方面来简要谈谈自己的看法,然后请大家分享各自的阅读体会。
这本书是典型的政治文化研究,谈论了美国国家身份、美国例外论、暴力这些主题。史密斯-罗森堡从18世纪末的政治杂志与小说中,发现了美国政治精英试图塑造三种国家身份:共和国公民、美利坚人、共和绅士。这些国家身份都是以在国内民众中树立“他者”而构建起来的。然而,主体与他者的边界不明,他者模糊,主体也失去应有的稳定性。为了强化国家身份认同,明确主体与他者的差别,精英以修辞暴力对待反叛的农场主、女性、土著人与黑人奴隶。塑造他者以构建国家身份是本书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则在于,把这些塑造的形象、创造的话语、经过排练而呈现的表演一一加以解构,以达到最终解构美国例外论的目的。这是本书的学术贡献所在,借助文学批评的方法、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重新解读寻常可见的史料,进而提出创见。
国家身份问题就是一个“我是谁”的问题,国家身份的形成是国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重要内容。我们前面读过的《我们失去的自由》和《山巅之城: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俗人布道》这两本书也都涉及这一问题。对内而言,统一的国家身份认同能够凝聚一国人民,维持国内统治秩序的稳定;对外而言,国家身份认同则指导一国对外政策,提升国际地位与实现国家利益。对美国这样一个缺少悠久历史,而又有着丰富多样的种族、族裔、文化、宗教的国家来说,国家身份问题尤为重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提出国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强调18世纪中期印刷文化的发展是现代国族主义的基础。他的观点已为很多史家所接受并深化,他们关注公共印刷文化与国家身份形成的关系,具体包括报纸、政治和文学杂志、小册子和小说。但也有学者提出,印刷文化是国族主义的实践形式,并不是结果。“日常国族主义”(everyday nationalism)概念的出现,更是支持了这一挑战。这一研究路径考察印刷话语背后的文化情感。这些史家关注街头剧院、游行与其他公共节庆,公共演说,甚至是消费行为。这些研究考察的都是对内而言的国家身份。也有学者关注对外而言的国家身份。王立新老师的一系列论文,比如《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我们是谁?威尔逊、一战与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关注的就是这一层面的问题,也就是美国在国际上如何定位自己,扮演什么角色。由此可见,《这个暴力的帝国》思考的是对内而言的国家身份,即美国人应具有哪些共性,才能实现国内的和谐一致。同时,作者的立论是建立在政治印刷文化推动产生了国家身份认同这一假说的基础上的。
但是,与已有研究都在考察美国建国初期国家身份的形成不同的是,本书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的是国家身份的不稳定,想要颠覆对当时形成美国国家身份至关重要的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强调,美国在政治制度、社会平等、民众权利等方面较之欧洲(尤其是英国)是独特的、甚至是优越的。美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特殊性,由此产生的美利坚共和国也比历史上任何政府都优越,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在美国史学史上,美国例外论不仅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题材,还一度成为一种研究范式。特纳的边疆假说可以看作美国例外论研究范式下的典型。现在美国历史学家不再使用例外论的研究范式,甚至很多史家批判例外论,包括我们上一次读的丹尼尔·罗杰斯的新著《山巅之城》。尽管如此,历史学家彼得·S.奥努夫(Peter S. Onu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还是肯定美国例外论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帮助独立后的美国人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与国家身份。置于这一学术脉络,我们看到,史密斯-罗森堡的立场是批判美国例外论。罗杰斯是通过解构附着在“山巅之城”上的起源神话,来批判美国例外论。史密斯-罗森堡也是采用解构的方法,她解构的是美国建国初期政治精英创造的三种国家身份。她的解构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解构主体,第二步是解构他者。既然主体和他者都有悖于所宣称的话语,那么这一话语本身也就无法成立了。
该书的另一主题正如标题所示,即强调暴力在美国国家身份形成中的核心作用。近年来,美国早期史家非常关注暴力问题,尤其是美国革命中的暴力问题。历史学家霍尔格·霍克(Holger Hoock)在他的《独立的伤痕:美国的暴力起源》(Scars of Independence: America`s Violent Birth)一书中曾给“暴力”概念下过定义:“使用体力想要杀人,或者对人或财产造成伤害”,同时也包括“心理暴力,即利用威胁、欺凌策略和暴行,来让别人感到恐惧,影响他们的行为和决定”。这样的暴力总是与普通民众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想起美国革命时期革命者对效忠派所施加的人身和财产伤害,以及19世纪30年代北方民众反对废奴主义者的袭击行动。与这些不同的是,作者在书中多次指出,她所谓的“暴力”是“修辞的和字面上的”暴力,可以说是精英的暴力。结合全书内容来看,就是东部中上阶层根据自己的需求,在政治杂志与流行小说中把西部农场主、女性、土著人、黑人奴隶“他者化”:把西部农场主塑造成缺少男性气概的花花公子,把女性塑造成沉溺消费、任性的妻子和女儿,把印第安人塑造成不事农耕的野蛮人与嗜血成性的杀戮者,把黑人奴隶塑造成失去自由、没有教养、退化的人种。其中,女性是比较特殊的群体,她们既是暴力的对象,也是施暴的主体。正如本书第二部分第5章所论述的那样,有文化的中上层女性作家以撰写小说的方式,参与了把土著人塑造为野蛮人、把美国人塑造为文明人的“暴力”。其他群体则因为缺少必要的教育程度与发声渠道,而几乎只是被“他者化”的对象。这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
本书使用的主要史料是18世纪末的政治杂志与小说。除了这些文字材料外,作者还使用了图像和物质材料,史料种类可以说比较丰富。比如,书中第6章评论美国新兴商人阶层扮演绅士的努力与结果时,作者分析了肖像画、建筑样式与装饰风格以及家具等。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利用了很多理论来帮助阐发观点。具体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多种理论的熟练使用,体现出作者深厚的理论素养与高超的驾驭能力。作为本书核心概念的“他者”就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在后结构主义思潮下,成为文化批评的重要命题。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西蒙·波伏娃用这个概念来批判父权制社会,她在《第二性》中提出了女性是他者的著名论断。他者概念也被运用到后殖民批评中,来分析帝国主义,帝国与殖民地的压迫关系,比如萨义德的《东方学》。利用他者概念来分析、揭露他者化中形成的霸权和压迫,是后现代主义对文学批评领域影响的体现(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我们首先要理解这个概念,才能理解作者在本书的构思与布局。本书为我们展现了如何利用跨学科的理论来提出新的历史阐释的范例。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我觉得首先有必要把概念说清楚。“national identity”究竟作什么讲,又如何翻译?“国家”是个挺麻烦的词。中文的“国家”是三位一体的,包含土地、人民、政权。英文中“国家”却是三个词,country、state、nation。三个词有共同点,但也有明显的差别。“country”主要指一个地域范围,当然,在这个地域范围里住着人,在这些人上面还有一个统治的主权者。“state”也有一个地域范围,但主要指控制这个地域及其居民的政权。“nation”也离不开地域范围和政权,但主要指某个主权者统治下的居住在特定地域的人民。很显然,“country”侧重的是地域,“state”侧重的是政权,“nation”侧重的是人民。另外,在美国的历史语境中,“state”指“州”,而“nation”则指联盟,是两种不同层级的国家。这又增加了含义上的复杂性。所以,“national identity”在中文里翻译成什么呢?是“国家认同”,还是“国族认同”,或者是“国族身份”,要视情况而定。讨论的时候,大家要对这个概念多留个心眼。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指的是“nation”,也就是“国族”。他是从“nationalism”(国族主义)这个角度来讲“国族构建”的。
蔡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这本书主要从“他者”的角度来讨论国家身份,这一类的书其实是挺多的。作者在“前言”中特别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想这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史学在研究取向上发生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即“身份转向”。史密斯-罗森堡早年是做妇女史出身的,在70、80年代是妇女史领域的一个重要学者。这本书则是2010年出版的。在这期间,这批妇女史出身的学者在研究路径有一个共同的变化,就是从妇女史转向性别史,再转向身份政治,把性别作为众多身份中的一种。包括史密斯-罗森堡在内的一批研究性别史的学者,都强调身份(包括国家身份、性别身份、阶级身份、族裔身份等)的不稳定性。这是一个共同的特征。总体而言,身份研究到90年代以后就带有很多后结构主义的特征,即强调主体的不稳定性,强调身份之间的交叉性、重叠性和模糊性。所以,看到史密斯-罗森堡这本书,我首先想到的是妇女史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后结构主义冲击下研究取向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史密斯-罗森堡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李剑鸣教授:学术语境确实特别重要。林恩·亨特在《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中提到,当前国际史学有四大趋向,其中一个就是身份政治。林恩·亨特观察的对象主要是美国史学。在美国史学当中,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politics of identity)是一个非常大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原来的gender、race、class这些概念,变成了一个更重要的分析范畴。刚才蔡萌讲的“身份转向”,在美国学术界的确特别突出,研究性别、族裔的学者,大多转向了身份政治。要读懂这本书,就必须了解这一学术语境。史密斯-罗森堡也很重视学术语境,她写了一个序,一个导论,都谈到了学术语境,力图把她的研究“学术语境化”。作为一个很成熟的学者,她似乎很看重这本书,因为这是她一生学术事业高峰时的作品。
话题一: 谁来界定美国的国家身份?
蔡梦竹(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我想说两点。第一,刚刚迪秋师姐在陈述中多次提到了“政治精英”,我们有必要把书中这一概念作进一步的澄清,界定一下作者笔下政治精英的具体所指。我觉得作者主要谈论的是东部的、城市的商业精英,她反复使用的词是“资产阶级”(bourgeois)。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就在于,在传统的共和社会中,他们作为“逐利阶层”是被污名化的,也是被排挤在政治权力中枢之外的。但到18世纪末期,这一群体作为一个新兴的、强势的阶层已经崛起,所以他们需要借助这些杂志作为自己的喉舌和舆论工具来重新改造传统的共和主义思想,进而确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崭新的国家身份和秩序。第二,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自觉地想起上次读书会上李老师提到的关于构建国家身份、国族认同存在两个向度——即内在的和外在的向度。这本书主要侧重于“他者”形象的构建,所以更多的是依循外部这一路径。作者讨论的一个重要基点就是,美国建国之初缺乏共同的历史文化纽带,内部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和多样性,并非铁板一块(monolithic),因而聚讼难休。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之下,这些精英们需要构筑一些“他者”的形象来维护表面的和谐和同质性。
夏刘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刚才梦竹谈到政治精英的问题,书里面主要强调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北方的政治精英,主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宾州的费城、纽约州的纽约市。这些地方的报纸、杂志相对比较集中,而且比较发达。但是,既然谈论national identity——国家认同、国族身份、国族认同也好,作者对南方的精英关注比较少。书中谈及南方政治精英的材料相对来说很少。据我的了解,弗吉尼亚尤其是在威廉斯堡、里士满等地方,有好几家报纸、杂志,相关材料很丰富。既然是国家认同,无论是材料上,还是视角上,她对南方,哪怕是南方的政治精英,关注的也不太够。
林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其实作者讲的是sectional nationalism的问题,即地区性的国家主义,也是我们以前讨论过的“扬基”问题。作者把波士顿、纽约、宾夕法尼亚这些地方政治精英的国家想象当成美国的国家想象。这些东部人士自认为是这个国家的代表,他们也不断四处传播自己的观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个暴力的帝国》描述了他们不断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我们还可以思考美国历史怎样被北方化、东部精英化,东部精英的历史如何成了整个国家的历史。
夏刘锋:另外,尤其在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问题上,有些北方州的政治杂志把南方州的种植园主和中等阶层描绘成堕落的、腐化的,把南方也作为一种他者来描述。特别是书中第388到402页,“自由的暗影”(Freedom’s dark shadow)这一部分集中谈到这一问题,那么我想问的是国家到底包不包括南方的种植园主和中等阶层,以及最下层的奴隶。
话题二:谁是“美国人”?
李剑鸣教授:这本书分成三大部分,每个部分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这三个独立的主题牵涉到美国早期,也就是革命后到建国初期美国人国家身份构建中的三个核心问题。这个三部分分别讲的是什么?作者的思路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讲?现在大家还没有谈到这些问题,就开始大讲这本书的缺点,不利于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刘雨君:第一部分主要是从建国初期的几种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入手,如古典共和主义、商业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从女性和西部农场主身上所反映出的一些特点,不符合这三个最主要的政治思想和思潮,从而揭示他们为什么会被排斥到主流的国族身份之外。第二部分主要是从原住民的形象入手,欧裔对美洲原住民有一种矛盾的看法,一方面认为他们是勇敢的、未受污染的、最纯粹的高贵的人,具有共和国公民的美德,符合共和主义价值观;另外一方面,欧裔认为原住民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他们残忍暴虐,不文明。作者借大众对原住民的矛盾看法来展现建国初期美利坚人对原住民“他者”形象的建构。第三部分涉及女性与有色人种。通过政治杂志和小说折射出当时美利坚人所排斥的东西是什么,比如女性缺乏男子气概,受奴役的有色人种没有自由。通过这种方式,欧裔精英抨击、污名化西部农场主、女性、原住民和有色人种,把他们视为“他者”,进而展现建国初期的“暴力”。
李剑鸣教授:大家的思路不要被她所说的“他者”误导了。这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什么?作者强调美国早期社会具有高度的多样性,革命后的美国人没有共同的历史,没有共同的宗教,没有共同的族裔来源;在这种共同性很少的基础上所建构的国家身份,自然就具有不稳定性(instability),于是他们只得构建很多个“他者”,以帮助他们维持国家身份的稳定性。所以,作者的主旨不是讨论“他者”,要讲的是国家身份本身是什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内在的矛盾是什么,不稳定性的缘故是什么。尤其是不稳定性促使美国人去寻找“他者”,用这些“他者”来帮助他们来划出国家身份的边界,以取得稳定性。可是,这个边界又很难划清楚,“他者”和主体之间有交界和交叉的部分。尽管有“他者”的帮助,但并不能完全消除身份的不稳定性。
蔡萌:史密斯-罗森堡注重“他者”,这种方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研究国家认同的形成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这本书从“他者”的角度考察,用了这么大的篇幅,我觉得有点偏激,只是讲了一半的故事而已。
鲁迪秋:书中的三个部分分别处理了不同的范畴。第一部分处理的是性别和阶级,第二部分处理的是种族,第三部分处理的还是性别和阶级。东部政治精英想从阶级、性别、种族这些方面来构建国家身份的边界。他们想要构造的是一个中上阶层的白人男性的形象.
李剑鸣教授:简单地说,这本书要讨论的是,建国初期的美国人所想象的美国人是谁,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大家要从书里把作者的答案找出来。这是作者的出发点,也是她的主旨。她讨论了那么多问题,用政治杂志上的文献,用小说作为史料,就是要讲清楚,革命后美国人所界定的美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焦姣(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刚才谈到的三种排除的方法,让我想起李老师一开始讲的nation-building和state-building两个概念。不光仅仅是在中文的概念里很难区分,即使在英文研究的方法里,nation-building、state-building在方法和史实上也很难完全剥离开来。这种修辞上的剥夺很大程度上总是跟另外两种形式的排除联系在一起。以前我们上王希老师的课,做公民权的研究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公民权必然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身份。这两者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没有办法区分开的。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翻译问题。
林斌:这个问题在书中展示的只是一部分。在内战前夕,北方继续对南方奴隶制进行妖魔化的宣传活动。最典型则是“slave power conspiracy”,即南方奴隶主试图把奴隶制传到北方去,控制联邦政府。在内战前,南方历史经历了不断被塑造和他者化的过程。有几本书就详细描述了这段历史,譬如Susan-Mary Grant所著North over South: Northern 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Identity in the Antebellum Era。
林斌:这也就忽视了南方的联邦主义者。
夏刘锋:她给予南方的关注很少,但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南方,或者从南方视角出发来研究国家认同问题留下了不少可进一步发挥的空间。
李剑鸣教授:这本书里提到,东部精英把“农民”作为一个“他者”。可是,她是在泛泛地讲“农民”吗?她讲的是马萨诸塞西部的farmers,而不是一般的“农民”。它为什么要在讨论共和公民(Republican citizens)时,专门把马萨诸塞西部的farmers拿出来说事呢?这就牵涉到马萨诸塞西部在革命时期的情况。在整个革命时期,马萨诸塞西部的农场主始终都在唱对台戏。在革命开始时,马萨诸塞西部就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地方。那里的居民认为政治权力被东部的富人把持,“伯克希尔立宪派”强调民主,要求建立尽可能地接近古代民主的体制,人民直接控制政府,政府直接依赖于人民,开销小,结构简单,要让普通人能懂是怎么回事。他们觉得,东部的富人却想把政府弄得挺复杂,让普通民众不明就里。波士顿在东部,是马萨诸塞州议会的所在地,东部的富人就近控制了州政府。所以,西部人不服,甚至要求废除分权的政府体制,关闭当时的县法院。在东部人看来,马萨诸塞西部农场主就是想搞无政府状态,不要政府,不服权威,不要法律,实际上就是造反。后来出了“谢斯叛乱”,更证明东部人的判断是对的。在东部人看来,西部农场主有两个特点:一个叫licentiousness,意思是无法无天,不服权威,不讲秩序;第二个叫levelling spirit,也就是“拉平”,铲除一切差别,因为他们穷,就要把所有人变得一样穷。在东部政治精英构想Republican citizens的时候,这些人就成了最好的反面参照,被建构为“他者”。共和公民不是不讲秩序,不是不尊重权威,不是不尊重法律,也不是要“拉平”。所以,马萨诸塞西部的farmers处处与共和公民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和反差
夏刘锋:宾夕法尼亚中西部与马萨诸塞很类似,尤其在对新联邦宪法进行公共辩论的时候。中西部好多反对新宪法的人也认为东部精英制造了一个在他们看来非常危险的政府,这与马萨诸塞西部的农民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李剑鸣教授:费城制宪会议制造了两个很大的“他者”,一个是马萨诸塞西部的“谢斯分子”,第二个是罗得岛。制宪者指责罗得岛实行债务救济,发行纸币,议会只听民众的,也不派人来费城开会,说明他们就是一帮异端分子。人类认识事物、界定自身需要“他者”,这也是人类认识事物、界定自身的习惯。
王倩茹:刚刚有人提到,当时美国人在构建自己身份的时候,一边把欧洲人他者化,一边又对内说我是欧洲人,我和你们不一样。这其实是参照坐标不一样。和欧洲人相比,他们确实不是欧洲人,是在美国生活的;而对于印第安人来讲,他们的确是从欧洲来的。这是不是就可以说,他者只是一个用来认识自我的工具,并没有真的要把他者边缘化。
李剑鸣教授:作者在书里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者”是要被消除的对象。这就是说,“他者”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工具,而是一种现实存在的一种危险,要打击和消除。正是因为要消除“他者”,所以作者说美国人的身份建构具有暴力的性质。
王倩茹:就是说“他者”的被边缘化还是客观存在的。
李剑鸣教授:对这些欧裔美国人来说,不管“他者”的威胁是现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都说明他们意识到了这种威胁。对他们来说,想象的威胁就是现实存在的威胁;只是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它具有想象性。
鲁迪秋:李老师刚才讲的内容让我想到作者在书里说的一句话。她说,这些他者其实不过是美国人内心黑暗的一部分。他者和主体两者是融合在一起的,他们把自己内心恐惧的东西拿出来,夸大并边缘化,把他们当作他者。所以,他们越是想要驱逐那些他者,越是不可能驱逐。因为他者与主体其实是一体两面,是一个东西。
林斌:前面第一个问题是代表制的问题,这跟我们读过的《我们失去的自由》具有相关性。这是我一直强调的公权力的垄断。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政治精英们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程序,包括政治理论的创新和实际的政治构造,将权力不断集中到他们自己手中。这些政治精英本身有一种对制度建设和政治理论的迷恋,可以说继承了启蒙时代以来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州层面的政体构造和联邦层面的国家构建中,政治权力拥有新的合法化的外衣。可能这些构造的初衷是好的,不过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构建后,人民不断丧失他们原本拥有的自由。他们必须通过现有的政治程序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作者看到了这一过程,认识到人民的影响力不断遭到削弱。后来联邦党人更是强调和突出想象中的美国人民(American People),以取代州人民(People of States)。这种政治修辞有助于推动权力的再次集中。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国家和资本主义。我们需要理解两种资本主义,这本书中提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在17、18世纪,还存在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杰斐逊派共和党人就反对国家权力和商人、资本的结合,要求国家尽可能不干预人民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作者提到的是国家权力和私人利益相结合的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裙带资本主义。
林煜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我在硕士阶段关注过美国早期的奢侈与消费的问题,但远不及作者思考的广度与深度。她没有单纯地停留于奢侈消费的议题,而是巧妙地把日常生活与宏大议题的勾连起来,主动地把相关讨论延伸到了对国族身份的探讨,可见作者的史学功力与洞见。另外,我觉得,本书主要是从三组相互对立的关系入手,即市民与“农民”、男性与女性、欧洲人与印第安人,来讨论美利坚国族身份是如何建构的。但是如此一来,作者只关注了国族身份建构的内部面向,而忽视与回避了外部面向。王立新老师的文章《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也关注美国的国家身份问题,认为美国早期建构国家身份的做法是将欧洲他者化,排除自身的欧洲属性,否认源自欧洲的身份特征。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暴力的帝国》所描绘的三对关系背后的共和主义价值观,性别观念,种族优越论均有鲜明的欧洲思想渊源。特别是面对印第安人的时候,美国人不断强调自身鲜明的欧洲属性,这显然与将欧洲他者化的做法是相悖的。也就是说,他们既想强调欧洲特性,又要极力与欧洲划清界限,形成了既是欧洲人、又不是欧洲人的“摇摆”窘境。在面对这样复杂的关系时,作者显然没有很好地处理“即欧非欧”的困境,也许是在刻意回避这一问题。当然,这不光是作者所要面临的难题,同时也是美国人国家身份构建的僵局。另外,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所谓的白人精英,他们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了强势权力。通过把控话语、掌握土地与占有财产,他们一步一步地将各种各样的权力集中在了新生的白人共和国(White Republic)。作者也在暗示,看似白人精英展开了对话语霸权的争夺与对精致优雅生活的追求,实际上是实现了权力的回收和重组,并以此构建起整个国民身份认同。
第四部分:小结
李剑鸣教授: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这本书是一种经典的“回溯式”研究,也非常生动地诠释了克罗齐命题,即“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书的前言开篇就讲,在当前恐怖主义的威胁下,美国人把异族、异端、外国人、戴面纱的人看得极其可怕,极其恐怖,要提防他们,打击他们。这一切都是有历史的渊源的。书的结语又回到这个话题,说现在的美国人所感受到的各种“他者”的威胁,以及他们对他者的态度,在历史上都有先例可循。可见,这种研究正好体现了史学的“现实关怀”
“现实关怀”在英文里就是“presentism”,牛可老师翻译成“当下关切”。这种现实关怀或现时主义,对于历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能引导我们发现题材、界定题材,引导我们凝练问题意识,寻找解释的路径。大家在做研究的时候,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都会受到现实关怀的影响。当然,有的学者可能没有这种自觉的意识,不知道自己受到了现实关怀的影响。有的人则有过强的现实关怀,要用历史服务于现实,而不是让现实引导自己去思考过去。这两者都是极端的倾向。对于好的历史学家来说,应当比较自觉、比较清醒地意识到,现实关怀或现时主义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又会带来风险。尤其是它会诱导我们用现在的标准来诠释历史,用历史来服务于现在。所以,当我们寻找题材、界定题材和形成问题意识的阶段,现实关怀的参与是必要的、正当的;但是当我们进入到解读史料、构筑解释体系的时候,就要警惕现实关怀的干扰,要保持历史主义的意识,要用语境主义来提防现实关怀的不利影响。
在这本书中,史密斯-罗森堡所表现出的现实关怀过于强烈。她很明显地要用历史来诠释现在,要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这就导致她对美国早期“national identity”的解读有很多牵强的地方。第一,夸大了美国建国时期的差异性。其实建国一代有很强的共识,没有共识怎么可能建成一个新的国家?殖民地起来反叛母国是非常危险的事,前途不明,命悬一线,没有共识怎么可能冒这样大的风险?当时人正是基于共识,才造成了这么大一个事变,而且把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也牵扯进来,把它变成了一场国际战争,还花那么多精力去制定宪法,去讨论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其实建国一代也讲差异,但他们讲的差异不同于史密斯-罗森堡的说法。他们看到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地域、气候和物产的不同,因而人民的生业、宗教和政府也就不一样。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尽管有这么多不一样,但是最后13口钟能够同时撞响,这才是奇迹。史密斯-罗森堡夸大建国初期的差异性,目的是强调身份构建的急迫性,以及导致这种身份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
但不管怎么说,“回溯式”研究是有意义的,马克·布洛赫就曾说,历史研究本来就是“回溯式”研究。但是,这种研究方式也有风险,我们一方面要自觉利用,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借助历史学家的专业水准、专业标准、专业精神,要调动历史主义意识和语境主义意识,以防止现实关怀过度介入历史研究,对我们造成不利影响。
这本书的确存在一些不足。刚才大家谈到,她关注的是中东部城镇的精英群体,是他们关于国家身份的观念和想象。她不但没有顾及到南方的精英群体,而且也忽视了那些“他者”在国族构建中的积极作用。女性也好,奴隶也好,印第安人也好,其实都从正面参与了美国早期国家身份的构建,而不仅仅是“他者”。有人研究过印第安人的制度和生活,发现他们的传统对美国文化的塑造发挥了作用。还有人认为印第安人元素在美国宪法中也有体现。女性也不仅仅是“他者”,她们也以自己的方式在国家身份的构建中留下印记,比如“共和母性”的问题。这些都提示我们,如果从正面来看,这些“他者”也是国族构建的参与者(nation builders)。
正如我前面谈到的,史密斯-罗森堡的研究主要是补充性的,属于“接着讲”的路子。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我们就能更恰当地把握它的意义之所在。
文稿 | 复旦大学 鲁迪秋

